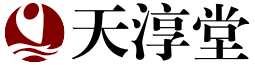人体发生病变,在邪正斗争、阴阳消长的过程中,从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出种种平衡失调现象,表现为寒热虚实表里脏腑气血等错综复杂的证候。当病变处于静止阶段证候也可以相对稳定;当病变处于发展变化的情况下,证候也随之变幻不定。每个证候的建立和证与证的界限,都是在疾病处于相对静止阶段,经过反复观察和方证对应才能确定。只有方证确定之后,辨证论治才能作为常规运用。实际上临床所出现的证候,非典型证候多于典型证候。所以,辨证既要掌握常规,又要知所变通,不墨守常规,否则也无法应付临床复杂多变的情况。因之对待各种不平衡现象,要求得平衡,既要掌握固定的辨证形式,又要进行动态观察,才能处理好一些复杂问题,也才有可能达到求衡的目的。
变,包括质变与量变。证候既是处于一定阶段的本质反映,证候的变化,当然存在量变与质变问题,所以求衡不仅要准确地找到其不平衡的所在,而且要衡量不平衡双方各个层次的失调程度和比例,才能恰如其分地进行有效的平衡协调。既然存在着量变与质变,辨证要知常达变,就必须探讨辨证定量及质量变换关系。众所周知,客观事物变化都存在量变与质变,没有脱离量的质,也没有脱离质的量,质反映量、量的关系也反映质的关系。《伤寒论》为方书之祖,辨证之经典,论中所述各证的某些症状,不但具有量的概念和意义,并显示出证与证的质量变换关系。因此,要探讨辨证如何定量和质量变换关系,从而知常达变,从伤寒的辨证方法中是可以得到启发的。
一、主症在证候中的地位和分量
《伤寒论》把大量的个别经验、包括教训进行分析、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由经验上升到理论,并汲取《素问·热论》有关热病的理论,对条理化、系统化的经验进行综合和演绎推理,成为六经辨证方法,用于指导治疗,使对症下药过渡到辨证论治。对症下药的个别经验,只是认识事物的个性,个性必须通过分析、比较、分类、归纳,从中找出共性,才能认识到疾病中具有共性的证候。以热病常见的发热为例:伤寒表证发热,“头痛……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应作恶寒)无汗而喘”;阳明里热证发热,“大汗出……大烦渴不解,脉洪大”;阳明湿热证发热,“头汗出,身无汗,齐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阳明里实证发热,“潮热”、“汗出不恶寒”、“短气腹满而喘”、“手足濈然汗出,大便已硬”等,都不是只看到个别症状,而是已从一些症中找到了它的共性。故治疗就不仅仅是针对个别症状,而是要“观其脉症”、“随证治之”。伤寒表证发热,用麻黄汤发汗退热;阳明里热证发热,用白虎汤甘寒清热;阳明湿热证发热,用茵陈蒿汤清利湿热;阳明里实证发热,用承气汤苦寒泄热,都突破了见热治热的对症下药。辨证既要凭依症状,每一证都是由几个能反映疾病本质的症状所组成,但具体到某些证候,则是有的反映本质见症,有的不反映本质,尤其是假寒假热假虚假实一类证候,现象与本质恰恰相反。所以,只有通过个别症状的比较、归纳,找到某些症状的共同本质才能确定一个证候,也才能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由于证候中的所有见症,有的反映本质,有的不反映本质,故单凭个别症状用药,不但不能普遍适应,并有较大的盲目性;如果只看到一些非本质反映的症状,用药只能适得其反。《伤寒论》各证所列举的症状,都是能反映疾病本质变化的症状,一些非本质反映的症状一概不予罗列,这样,就避免在辨证上主次不分。日本汉方医学大家大冢敬节认为《伤寒论》各证所列举的症状都是主症,“主症比如常在其家的主人”,其他可有可无的症状则为客症,“客症比如客人之来走无定”。这也说明主症是由疾病本质所决定的,客症不是疾病本质的反映,因而是可有可无的。主症既由疾病的本质所决定,多一症少一症,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实质上就包括质变。
例如:呕吐一症,伤寒表证“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此证之呕吐因外邪所扰而致,呕吐不是主症,故只用麻黄汤发汗解表,其呕自止。表邪传里,“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此证寒热身痛未罢,并见心下支结而呕,虽为微呕,亦为表里俱病,呕吐、心下支结均应视为主症,治此用柴胡桂枝汤表里双解,着重配合黄芩、半夏清热和胃,降逆止呕。前人认识疾病只能凭依症状,而相同的症常可出现在不同证候中,从辨证必须分清主次来看,每一症状出现在不同证候中就有着不同的地位和分量。由此可以看出,辨证分主次与辨证定量具有一定的关系,一个证候的定量,就是要抓住证候中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主症,只有与疾病有本质联系的主症才有量的意义。
二、主症的变化揭示证与证的质量变换关系
《伤寒论》,一是抓住了热病各证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主症;二是掌握了热病过程中的质量变换关系。因而,把热病所见各证按三阳(太阳、阳明、少阳)三阴(太阴、少阴、厥阴)六经分为六大类,这样不但便于分析各种证候的发病部位和性质,而且便于掌握六经合病、并病及传经、直中等传变规律。如病在三阳经,太阳为表、阳明为里、少阳为半表半里,三阳经所见各证,都有固定的主症可辨。正由于抓住了主症作为辨证依据,故具体对待某一个证候究竟在表在里、属寒属热、或表里寒热夹杂,都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断出来。如“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寒多热少(原文误作热多寒少),其人不呕,圊便欲自可”,此证发热恶寒如疟状,从其人不呕,排除病在少阳;圊便欲自可,排除病在阳明。这就说明病邪仍然留滞在太阳阶段,仍属寒邪在表,并未化热传里。如果抓不住各证与疾病本质有关的主症,弄不清证与证的质量变换关系,是无法作出寒多热少的结论的。伤寒病传三阴经,由于阳虚寒胜,多见恶寒厥逆。如阴证转阳,则可出现发热,如“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伤寒病入三阴,其后要看正气能否来复,阴证能否转阳而定。转阳的标志是发热,这种发热是一种“矫正”现象,如果厥逆日数多于发热,可以显示质量变换关系,故伤寒病后期,也就是以发热、厥逆两个主症来观察分析人体的阴阳消长变化的。
临床上所见证候,静止的、孤立的一个证候不与他证相涉是很少见的。故辨证,既要对当前的证候作出正确的判断,又要掌握当前证候的来龙去脉。《伤寒论》通过证与证之间的质量变换关系,摸清了各证的传变规律。所以,运用伤寒六经辨证方法,不但可辨明当前证候,而且随着证候的转变,并可预见疾病发展变化的趋势。如“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伤寒传经,一日一传,不过是举例而已,究竟传与不传,还是要从各证的质量变换关系来看,所以,没有出现“腹满而吐,食不下”等太阴证,“其人反能食而不呕”则为三阴不受邪,病邪仍然留滞在太阳阶段。
临证如果抓不住主症,不明确各证的质量变换关系,如遇到错综复杂的证候,则将技穷束手。如“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此证前误在用下法,下后仍有颈项强、胁下满痛,没有从小便难、身黄、饮水则呕等脾虚停饮之证看出病已转属太阴,故一误再误。证之未下前就脉迟浮弱,虚象已露;下后再与小柴胡汤,则虚象毕现,故产生气虚下坠及进食则引起呃逆等后果。仲景此条虽然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也充分说明在病情转变过程中,遇到错综复杂的证候,就必须注意抓住那些能反映疾病本质的主症,撇开那些非本质反映的次症,根据质量变换关系,随时改变辨证结论。
如上所述,主症在证候中占有一定的分量和地位,主症是对一切症状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症状。从主症与主症的相互变化中就可掌握质量变换关系。辨证能抓住这两点,既有常规可循,又不墨守常规。对待复杂多变的证候,就能游刃有余。由于一个具体证候的出现,往往同时具有几个或十几个症状,其中有的是主症、有的是可有可无的客症,如前所举麻黄、白虎、茵陈、承气四证见于临床,决不只是《伤寒论》所述的那些症状而不再出现其他客症。辨证如果分不清主客,机械地对号入座,那只能是症状的相加和拼凑,不可能知常达变、求得平衡。一般都认为中医辨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没有原则的灵活就会灵活无边,无常规可循;没有灵活的原则就无法应付复杂多变,只会墨守常规。所以,要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就必须知常达变。《伤寒论》辨证用药的常规,如六经所属各证的证治不过二十多条,大部分条文是讲变通的方法,包括误治后救逆的方法。如何知常达变,《伤寒论》已为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
由此可见,知常达变就是平衡理论具体运用的必要措施。平衡和知常达变虽不代表中医的理论思维,的确也是中医临床逻辑推理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