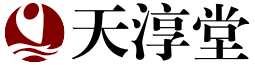杜氏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中医古籍汗牛充栋,而最精华者,当推仲景之书。因此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不但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崇尚实践,经验丰富。先后撰着了《伤寒论辨证表解》、《金匮要略阐释》、《伤寒论释疑》等书及《伤寒论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应用》等数十篇论文。对仲景著作的诸多问题,见解精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在如何学用仲景著作问题上,执简驭繁地提出“举纲、深究、致用、推广”八字。言简意赅,颇具指导意义,现简介如下:所谓“举纲”,就是要提纲挈领,抓住六经辨证的精髓,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六经是指导多种疾病辨证论治的纲领,是《伤寒论》的理论核心,故欲学习、研究《伤寒论》,必须首先弄清六经实质。
六经实质是历代医家争论的焦点。诸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六经实质进行了阐发。有以经络立论者;有以脏腑阐释者;有从气血探讨者;有主张阶段说及证候群说等等。可谓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杜氏上溯岐黄下逮百家,汇诸贤之精言,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六经及仲景接受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以中医整体观念为前提,阴阳学说为核心,气化学说贯穿始终,动态地分析多种外感热病的发病过程,脏腑经络营卫气血及其气化功能所发生的生理病理变化。仲景审证求因,据正气的强弱和邪气的盛衰定虚实;察邪留着的部位辨表里;审病邪与病性分寒热;视病势的进退测预后之好坏;进而确定治法、选用方药,形成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辨证论治纲领体系。使后学在临证时对于复杂多变的外感疾病以及一些疑难杂病有规矩可循。并为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纲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伤寒论》根据六经病总的病情、病机——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提出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八法论治,将113方及针灸、外治法等统辖于八法之内。在临证时主要通过脉、症、舌等,审证求因,分析和探讨病证的本质,然后针对病情进行治疗,处处体现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和治随证转的辨证论治特点。如太阳主表,但太阳在表之病邪循经入于太阳之腑——膀胱和小肠,则又形成太阳病之腑证,治疗就不相同。即使太阳表证,法当汗解,但因病因有异,体质不同,临床表现自有差别,从而又分太阳中风、伤寒和温病。其治法同为解表,但有解肌和营、开表逐邪及禁用辛温之别等等。领会六经本义,掌握六经辨证,才能理解原文,通晓《伤寒论》之精神,方可学以致用,纲举目张。俾六经实质面目显露,使后学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所谓“深究”,即深入研究《伤寒论》之原文、宗旨。欲深究之,必先掌握方法,不得门径,难以登堂入室,其要点如下:
1.要学习古代汉语,为正确理解原文打好基础,即“必先利其器”之意。《伤寒论》成书于1700余年前的东汉时代,屡经沧桑,文字、语法、词汇、术语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已非今比。如不了解古代汉语的特点,难免误解。文字方面,如“清血”一词,如若不知“清”通“圊”,乃古之厕所,名词活用作动词,“清血”即为便血,则茫然不知何解。又如“欲”字,在《伤寒论》中共有四种含义:
(1)作“想”字解,如11条之“反欲得衣者”即是。(2)作“已经”解,如213条之“此外欲解,可攻里也”。(3)作“将要”解,如65条“欲作奔豚”。(4)为虚词,如23条“清便欲自可”“欲”无解义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很多单词,皆与今有别,不可随文敷衍。文法方面,亦与今有间。《伤寒论》常用的方法如倒叙法,亦称兜转法,如27条“太阳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即是,文末方药,应接在“热多寒少”下,其意始通等。省文法,即相关联的条文详略互见,必须互参,如第1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首揭太阳经证之脉为浮,那么第2条言中风脉缓,第3条言伤寒脉紧,皆承前而略浮等。插叙法,即叙述主要问题的过程中,插入一段有关的其它问题,如108条“伤寒十三日……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此处“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即为插叙笔法,意在插叙虚寒性自下利的特征,以便和实热下利作鉴别等等。名词术语方面,很多有特定含义者,今已不多用,故应予注意。如“啐时”指一个对时,即24小时;“日晡所”即傍晚时;“下利”在论中包括腹泻和痢疾两种含义等等。皆应弄清,始明文意。
还应熟习古代哲学知识。“阳数七,阴数六故也”,若不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六七乃水火之生成数,单纯以奇偶分阴阳,则六七之数实难理解等等。
2.要结合《内经》、《难经》、《金匮》进行探讨,使之融会贯通。《伤寒论》之理论渊源于《内经》、《难经》。它不但继承了古代医籍的学术成就,且有新的发展。如《伤寒论》之六经源于《素问》,且又高于《素问》。《素问》之六经,只谈了热、实二证。在传经问题上,固守日传一经,循环相传的机械模式;在治法上,仅提出了汗泄二法。而《伤寒论》之六经,又论述了虚证、寒证,且证分表证、里证;以临床实际为据,不拘日期定传经;在治法上,八法俱全,体现了辨证论治之精神。
惟其如此,其内在联系仍不可忽略,如对“伤寒”含义的理解,则当依《素问》“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以及《难经》中“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等,从而确定了《伤寒论》中关于“伤寒”的确切定义。《金匮》与《伤寒》原为一书,因此二者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方证,详于《金匮》而略于《伤寒》,故在学习之时,更应上者互参,以印证原文,达到全面理解的目的。
3.要灵活学习,不可死于句下。《伤寒论》叙证简略,往往详于此而略于彼。全文言简意赅,较少华丽词藻。故在学习之时,既要字斟句酌,探讨每一字句的含义,又要举一反三,领会无字处读出有字来,始可成竹在胸。如“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若仅依原文“口燥咽干”为使用大承气汤的指征,恐难成立,非是急下,贸然用之,祸不旋踵。以方测证,是证当有痞满燥实的临床指征,方可投药。再如“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这里脉滑,里有热,是辨证的关键所在,点出了本条属热邪内郁,阻碍阳气不得外达而致的热厥,故用白虎汤直清里热为主。口渴,舌红苔黄,口鼻气热等里热证也就意在上五字之中了。
4.参考注本,择善而从。《伤寒论》问世以来,自金成无己注解开始,注释阐发者多如繁星,其著述更是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6年,国内现存《伤寒论》之注释书其书名及书籍俱存者已达541家。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深入研究《伤寒论》的学术思想,颇有裨益。因此,在充分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参看各家之注,无疑是提高的一种好方法。但这些著作,不可能全部习颂阅览,应先参考其中较有影响的名著,逐渐达到博览。对于各注家的意见,应择其善者而从之。不过,“择善”亦非易事,有时须反复琢磨,并联系临床实际分析认识,才能逐步达到分辨注家意见的“善”与“谬”。杜氏认为应以下列注释阐发书为佳。
(1)依据原著编次加注: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陈修园《伤寒论浅注》、北京中医研究院之《伤寒论语译》、成都中医学院主编之《伤寒论讲义》第二版及第一版。
(2)对原著重新编次注解:
方中行《伤寒论条辨》、喻嘉言《伤寒尚论篇》。
(3)按方类证加注:
柯韵伯《伤寒来苏集》、徐灵胎《伤寒类方》、左季云《伤寒论类方汇参》
(4)据法分类加注:
尤在泾《伤寒贯珠集》、钱璜《伤寒溯源集》。
(5)按六经类证加注:
沈目南《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6)侧重于运气学说解释原文:
张隐庵《伤寒论集注》。
(7)集名家注解意见对原文加以集注:
《医宗金鉴·伤寒论注》、黄竹斋的《伤寒论集注》、日本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译释》。
(8)医案类:
《名医类案》及《续名医类案》的伤寒部分、许叔微《伤寒九十论》、曹颖甫《经方实验录》。
(9)对原著内容阐发增补:
朱肱《南阳活人书》、郭雍《伤寒补亡论》。
其次,近代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伤寒论》问题的专题讨论和体会文章,内容丰富多彩,可适当地参阅。
5.知其优缺,批判继承: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伤寒论》存在着不足之处,我们应该有所认识。对于不正确的论述,应批判地继承,不能兼收并蓄。这主要体现在其受尊经崇古思想的影响,如六经的排列次序,仍未摆脱《素问·热论》的影响等;受先秦学术界思想弊病——臆测性的影响,如“发于阴六日愈,发于阳七日愈”等等,将暂时不能解释的临床现象,亦勉强解释,其机理认为“阳数七,阴数六故也”,颇觉牵强。其次,《伤寒论》成书不久,即遭散乱,后几隐几现,辗转传抄,舛错脱漏难免。应根据临床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整理原文,才能弘扬和发展仲景学说。如2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此条“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说明未汗下之前,即有表证存在,未言恶风,当是省文。桂枝汤是治有汗之表证的,服桂枝汤是误治,下之亦属误治,所以未得病解,反增“心下满,小便不利”水气内结不行之里证,表里俱有邪郁,治应表里双解为宜,而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最为合拍。用桂、姜辛温发汗以解表,茯苓术燥湿健脾,合桂枝以化气行水,对水气内郁有卓效。而芍药为阴柔之品,不利于解表,又不利于化气行水,故应去之。况桂枝茯苓同用为仲景治水气痰饮最常用的配伍,共奏化气温阳行水及渗利之功。临床用之,屡验屡爽。故此条所述病证,无论从何处讲,皆不应去桂,而应去芍,原文当是错讹。如此等等,习颂时应明辨之。
所谓“致用”,即学“伤寒”用“伤寒”,以《伤寒论》的理法方药指导临床,解疑难。具体应用如下:
1.据证定经,分经论治:因《伤寒论》这六经,不单为伤寒立法,而为百病之法,是自临床中总结而来的,可以概括指导百病。临床各科疾病若病机证候与原文一致,皆可据其脉证表现分析其属何经,从而据六经之法而治。如属太阳者汗之,属阳明者清下,属少阳者和解,属太阴者温运,属少阴者回阳,属厥阴者寒热并用等。俱应明了,不管何科,俱应依法而施。
2.病与文符,照用勿疑:因《伤寒论》之内容是仲景临床实践的结晶,故许多条文所述病证,皆能在临床上得到印证。有的病例从病因、病位、病机到脉证表现皆甚切合原文内容;有的虽病因、病程与原文不一致,但病机证候却与原文所述相同,此时应对照原文,据原文所出方药,大胆应用,坚信勿疑,往往取得满意疗效。在临床上,杜氏常常遇到典型的桂枝汤证、麻黄汤证、小青龙汤证、大青龙汤证、五苓散证、三泻心汤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小柴胡汤证、大柴胡汤证、理中汤证、四逆汤证、当归四逆汤证等等,投予原方,皆取良效。
3.病情复杂,抓住主症:疾病之表现,繁简不一,与《伤寒论》所述各证完全相同有之;不完全相符者亦有之。诊治时应重视主症的鉴别与对照。只要主症与文中有关证候的主症相符,可做出相应的诊断,治疗大法即可相同。诚如103条所说:“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杜氏通过对《伤寒论》原文仔细分析归纳,结合临床实际,得出各种证候皆有一定的主症,亦如西医的各项客观指标。如太阳中风证的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伤寒证的发热、恶寒、无汗、身痛、脉浮紧;阳明腑实证的腹满、便闭(或溏垢)、潮热、濈然汗出;少阴寒化证的脉微细、但欲寐、手足厥冷等等,主症已备,即可做出相应的诊断和治疗。
4.主症已定,照顾副症、兼症及成因:在同一病情病机的基础上,除表现出主要脉症外,往往还可见到一些次要症状(副症)。如太阳中风的鼻鸣干呕;伤寒证的呕逆和喘;少阴寒化证的心烦、欲吐、口渴等。此皆从属于主症,其之有无,不影响辨治,可不予考虑。兼症则不然,它是在主症的基础上,夹杂有其它内在因素所致的症状。如太阳中风证兼邪入经输的“项背强”等,应在治疗时给予照顾,用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对于成因,可不必拘泥,只要有主症,即可应用。杜氏曾治一中年妇女,在劳动中被车轧伤腹部,出现腹痛、尿血。住院治疗后病情好转,但患者手足及胸部汗出绵绵不断,当时查腹中隐痛,脉缓,加上自汗,遂投桂枝汤,服后无效。
经询问大便情况,知自外伤后至今大便四日未行。据193条“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然微汗出也。”186条“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为阳明也。”见其手足胸部汗出不断,大便不行,阳明腑实已备,乃与调胃承气汤加桃仁,服后便通汗止,调理而愈。
杜氏运用经方的思路和方法,对于后学尤其是初学者确有启迪及指点迷津的作用。
所谓“推广”,即是对《伤寒论》要师其法,用其方,不可过于机械。要在临床中发展、提高,只有如此,才可弘扬仲景学说。具体推广之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抓住病机,辨证给药:《伤寒论》重视一方多用,异病同治。如四逆汤为少阴温经回阳的首方,用以主治少阴寒化证,但论中又把它作为治疗中焦虚寒的要方。两者病位不同,一属少阴心肾,一属太阴脾,但均属阳虚寒盛。该方对少阴有直接作用,对太阴是通过温肾阳而起到温脾土之作用。以此为契机,杜氏不仅重视继承,尤为可贵的是能发展。如他将桂枝汤应用于虚疟、虚利、虚损、荨麻疹、大汗等;四逆汤应用于胃脘寒痛、胃下垂、心功能不全、动脉闭塞型脉管炎、宫寒不孕等。弘扬仲景重阳气的学术思想,认为中老年常患的高脂血症,多属肾气渐衰,因而以仲景法为主补肾温阳活血,制成“柔脉冲剂”,用以治疗高脂血症。经临床及实验观察,其降脂效果优于国内同类药品,且无毒副作用,其成果荣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它如以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失眠,八味肾气丸治疗高血压等,突破了《伤寒论》原有范围,其论文先后在中日两国主办的第二届、第三届传统医学讲演会上宣读,受到了中日学者的好评,《健康报》对此作了报道。又如依“血瘀下焦”之病机,将桃仁承气汤治疗慢性肾衰及通经止孕等,皆取得良好的疗效,实难一一列举。
同时,《伤寒论》还重视同病异治,如同为心下痞,而因病因病机之不同,所用方药有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五苓散、旋复代赭汤、桂枝人参汤等。再如厥阴病篇提到的厥逆证,有虚寒厥逆、蛔厥、脏厥、血虚寒郁厥、寒犯肝胃、热厥以及冷结下焦、水饮内停、痰饮致厥、亡血厥等十种证型,治疗各异。说明《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并非简单的对症治疗,而是透过临床表现,探求疾病的内在本质,治病求本。杜氏据此用于临床各科的诊治,不断创新,如将肾病分为不同证型,依经方辨治(详后)。
2.师其法而不拘其法,用其方而不泥其方:《伤寒论》所建立的六经辨证大法、治疗原则以及方药、针灸等,在祖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和遵循。后世尤其近代对《伤寒论》的理法方药,有不少的补充和发展。杜氏不仅对《伤寒论》中的一些具体治法进行了改进和补充,对方剂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使《伤寒论》之方药更切合临床实际。如他对《伤寒论》中运用附子的20首方剂进行整理,从研究附子的功能着手,扩大了附子的临床应用。如用于:
(1)阳虚欲脱:无论外感内伤,如果累及少阴,出现阳亡欲脱者,以附子配炙甘草、干姜、肉桂等以力挽残阳;若病极重者,加人参以培补元气;若有阴虚见症者合生脉散;附子用量可在9~30克之间。
(2)阳虚恶风:
轻者以附子配桂枝、白芍;恶风怕冷甚者,应配高丽参、黄芪、白术;
(3)阳虚发热:真阳内虚,虚阳不安于内而外浮,甚者阴寒内盛,格阳于外,而见发热,以附子配干姜、炙甘草、人参等温阳益气药以助其力;格阳证当加葱白、胆汁、白芍之类以通阳气、破格拒;若长期低热病例,呈阴阳两虚者,以滋阴退热药中加入附子、黄芪、白术等温药,以阴阳双补。
(4)虚寒泻泄:
肾阳亏虚,命门火衰,脾胃失温,水谷腐熟运化失常,水谷下趋而为泄泻,可选用附子理中汤、附子粳米汤以温补命火,调补脾胃。
(5)肾气虚不孕证:
女子不孕、男子不育,若非器质性病变所致者,多由肾气亏耗、命火不足、肾精不充引起,必用附子,配以熟地、续断、巴戟、枸杞、艾叶、鹿角胶、鹿茸、紫河车等以温补肾命,壮阳益精。
(6)五迟、五软证:
乃在六味丸基础上加附子及肉桂、海马、巴戟、鹿角胶、紫河车等补肾温阳药,并佐用益气健脾之参、芪、术、苓之属。
(7)肾脾阳虚水肿:
肾阳亏虚,不能温化水液,脾失肾阳温暖而不能输运水湿,致水湿泛溢为患,杜氏常以附子配茯苓、泽泻、桂枝等为主治疗。如尿不利者,可酌加澄茄温化行气以助利尿之功;水势过重,全身皆肿,可酌加葶苈子以逐水。
(8)寒湿痹证:
凡肢体关节肿胀、疼痛、局部发凉,或局部虽发热而同时恶风、屈伸不利、缠绵难愈、无明显里热征象者,均可用附子,并配以川乌、草乌、桂枝、细辛、灵仙等温阳散寒,胜湿止痛,通利关节。病久阴血亏虚者,可合四物汤而用之;肿胀明显者,酌入秦艽、防己、茯苓、苍术等。夹咽喉干痛者,去桂枝、细辛,酌加金银花、桔梗。
(9)上盛下虚之证:
肾阴阳两虚偏重,阳虚不安于本位,阴虚不能恋阳,致虚阳上浮,形成上盛下虚证。治宜桂附地黄丸,酌加怀牛膝、龙骨、牡蛎,以温补肾阴肾阳,引火归元等等,俱经临床反复验证,疗效甚优。